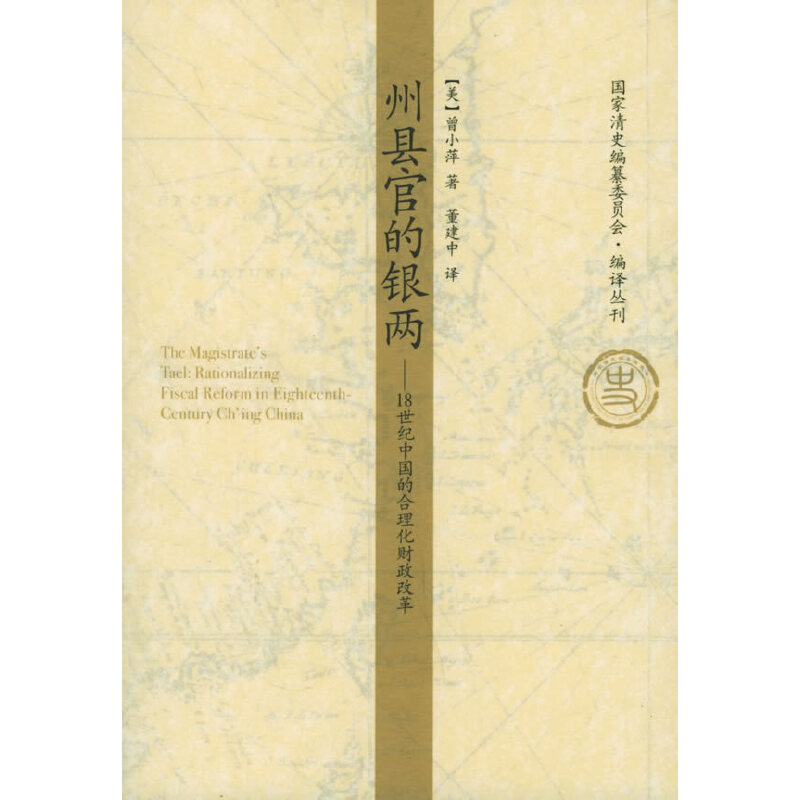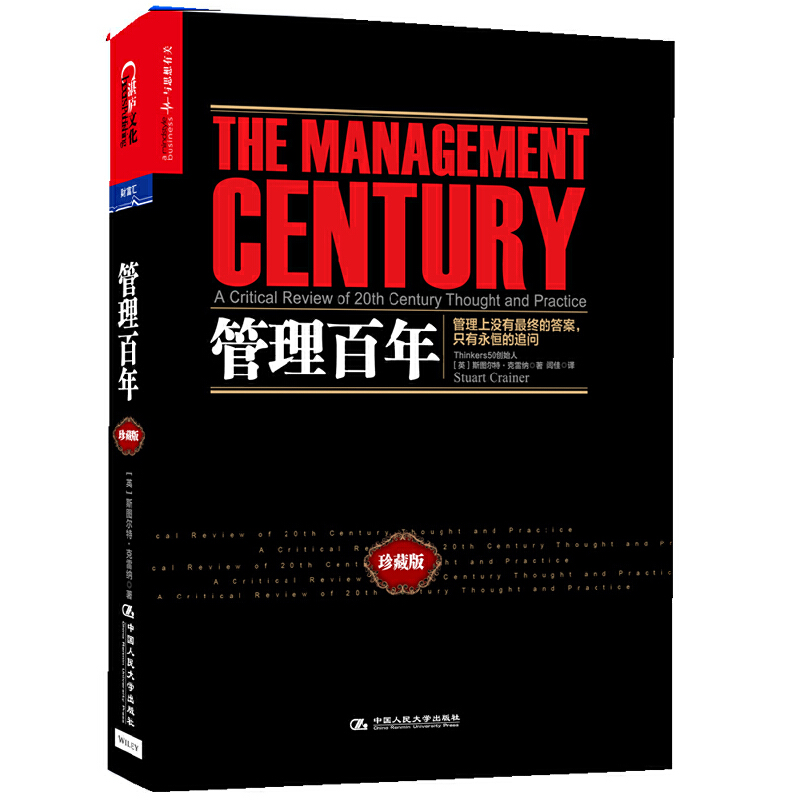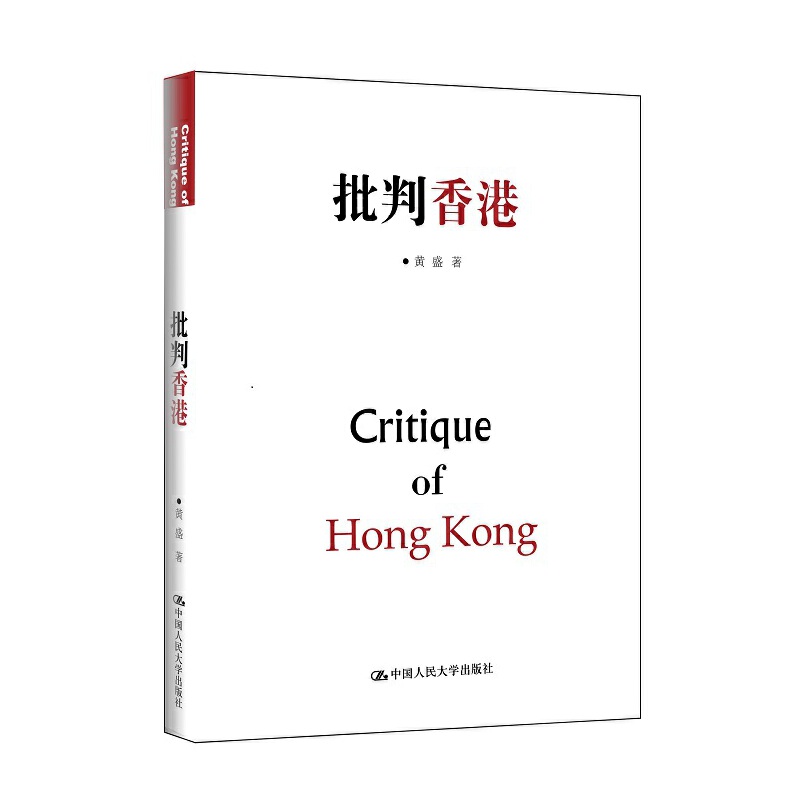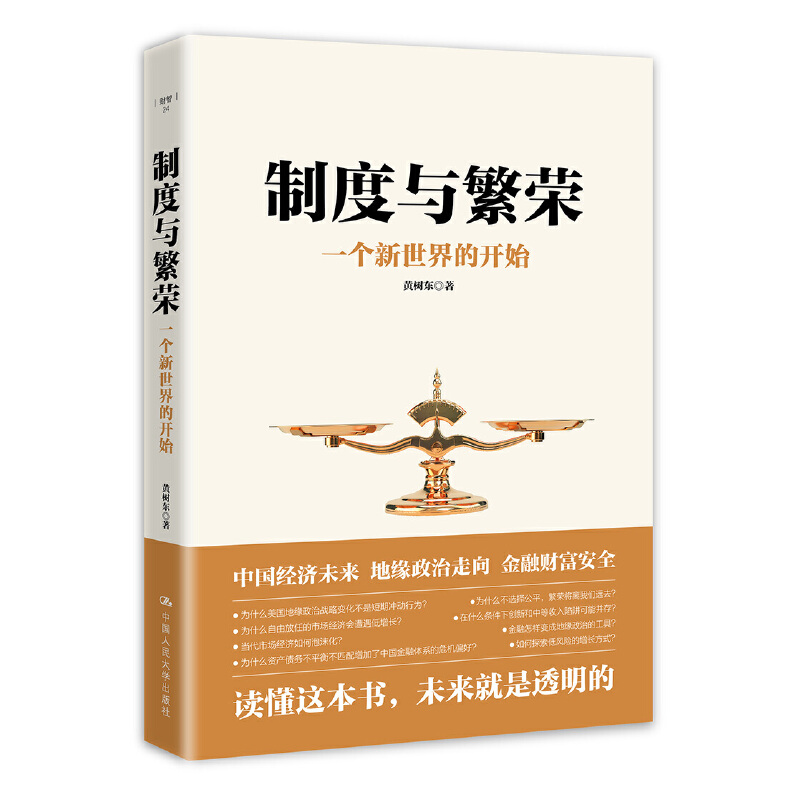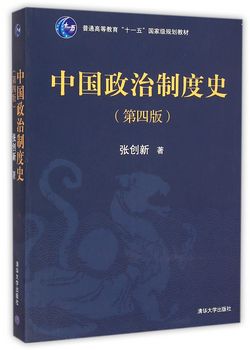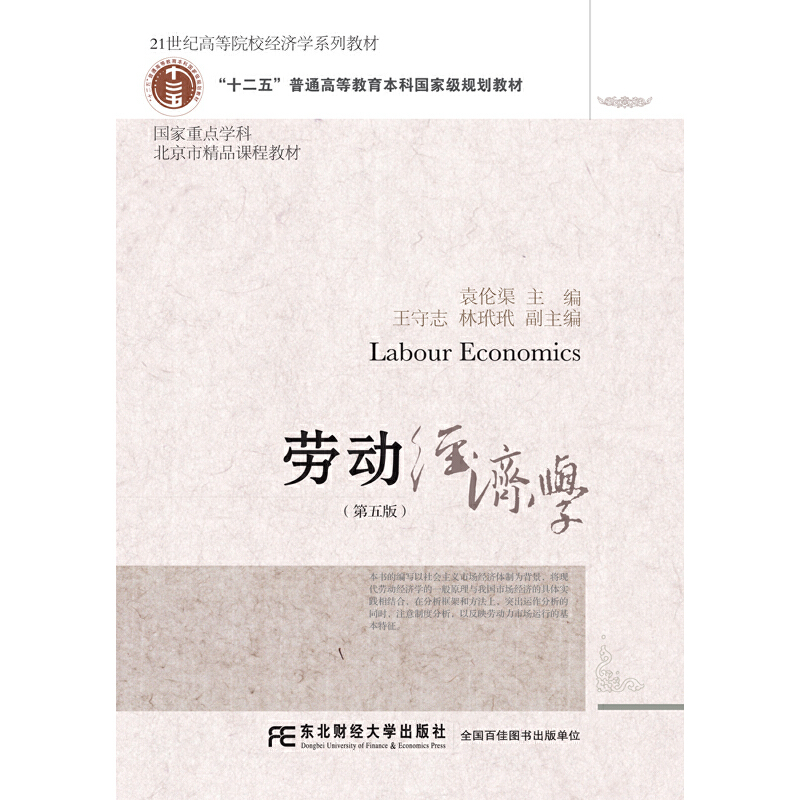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定价:¥22.00
作者: 曾小平
出版时间:2005-0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9787300062464
- 271657
- 2005-01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不久前,美国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都以鸦片战争第一声枪炮为开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1840年亦已成为评价国家过去历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由于仅仅关注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挑战之回应的失败,中国自身内在的演化进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领域,腐败的清帝国的幽灵铭刻在19世纪历史的编纂者心中,至今挥之不去。尽管我们不再说“不变的中国”(unchanging China),然而理解早期中国近代化经验的范式依然薄弱。腐败的帝国,由于陈旧的思想传统而与革新相暌违。结果,我们常常忽视这一历程的复杂性,并没有去探求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衰落的真正根源。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不久前,美国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都以鸦片战争第一声枪炮为开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1840年亦已成为评价国家过去历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由于仅仅关注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挑战之回应的失败,中国自身内在的演化进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领域,腐败的清帝国的幽灵铭刻在19世纪历史的编纂者心中,至今挥之不去。尽管我们不再说“不变的中国”(unchanging China),然而理解早期中国近代化经验的范式依然薄弱。腐败的帝国,由于陈旧的思想传统而与革新相暌违。结果,我们常常忽视这一历程的复杂性,并没有去探求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衰落的真正根源。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进行财政改革,以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臣民与统治者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调和作用但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他们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并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进行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世纪、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线模糊不清;在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他们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这使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加剧。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套财政制度,它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要求的财政制度。
清初财政改革事业的顶点是“耗羡归公”,这是在第三任皇帝即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实施的。各省官员被授权对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钱粮征收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即火耗),火耗存留在当地省份作为官员的“养廉”和“公费”。养廉银使得官员薪俸有了根本性的增加,同时可以使用公费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以及实施有益于当地的工程项目。
尽管火耗归公的概念简单,但它对中国财政管理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官僚体制内部,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足够的费用,消除了已经制度化的政府腐败。有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官员能够对地方开支进行预算并致力于地方建设工程的长期规划。此外,有了收入的保障,地方政府能够把许多服务及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而这些在帝国统治前数十年或被忽视或被委任于私人。
新财政制度所要解决的许多是前朝的遗存问题。明朝也曾多方努力消除腐败,但是除了“一条鞭法”的改革外,对重建国家财政机制没有什么建树。税收的货币化,这是“一条鞭法”的重要目标,是引发清初改革的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两个王朝在政府运行方面的差异大体可以解释清王朝为什么有能力在财政机构方面进行如此激烈的变革。
尽管明清两朝的官僚体制结构相同。但在明朝,意识形态的诉求(ideological appeals)在官员考核以及决策方面,起的作用要远为重要。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两个王朝皇帝的地位。明朝因其废除丞相而闻名,此举普遍被认为是帝制晚期对自治抬头的致命一击。尽管如此,大多数晚明统治者与操纵着中央官僚机构的那些文人们手中的傀儡相差无几。而另一方面,作为外族人,清初的统治者极少受传统君臣之礼的束缚,而且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帝王权威观念。与传统的儒学观念所强调的君主集权相比,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将皇帝置于权力更为集中的位置之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清初的皇帝们所起的直接作用是引进统治的新观念及新手段。到18世纪初,皇帝这一作用通过新制度的创立,比如奏折制度而得到强化,奏折制度既使皇帝得到信息,也增强了他对行政事务的控制。最后一点,与明朝相比,清王朝官僚机器本身更为集权,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的改革及保证皇帝对其实施的指导。
这些条件使18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解决中国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合理方法成为可能,但它们不能确保如此大胆的措施能够得以贯彻执行。处于被称为清朝盛世(High Ching)的每一位皇帝都是有才能及勤政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个性的差异以及各自统治期间政治气候的不同,对他们处理财政事务的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乾隆皇帝,盛世的最后一位君主,在统治过于宽仁的乃祖康熙皇帝和过于严猛的乃父雍正皇帝间极力寻求一种平衡。宽仁和严猛不单是这两位伟大帝王的不同风格。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满族人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统治。众所周知他拒绝打击腐败,但这可能是出于安抚占优势地位但还未顺从清朝统治的汉人官僚的需要。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则不再担心来自官僚或士人的责难。待他登极之时,中国统一,四海清平。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满族几近八十年的统治已经使他们在现实中除了清廷外别无忠诚对象,这些人的地位不但在于拥有地方上的财富和影响,也有赖于帝国赋予的官位与功名。雍正皇帝严刻、务实。但假如他统治的时期更早一些,那么他将不大可能采取实际上所采纳的合理化管理以及和腐败及士绅特权斗争的措施。
清朝盛世的和平与繁荣,部分要归功于火耗归公改革。不幸的是,尽管火耗归公对近代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终它还是失败了。19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斥腐败、被离心力量所破坏的国家,政府已日益衰落、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尽管如此,当真正了解在西方上升的世纪似乎冥顽不变的“传统”中国君主政体的时候,我们所探求的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会发生剧烈的改变:中国不总是如此。我们必须学会将帝制晚期的中国视为有生机的国家,为设计合理与高效的官僚体制自我的特有形式而奋斗。即便说火耗归公是一次失败的改革,那么我们也必须问个为什么。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视官僚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官僚阶层的道德堕落。现代批评家们也往往追随这一结论,面对政府严惩财政渎职官员的种种则例,学者们断言,清政府过于孱弱、懈怠而无法将之付诸实践,或是习惯势力过于强大,不论谁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都无法取胜。最终我们得出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中国是腐败的,所以中国是腐败的(China was corrupt because China was corrupt)。这样的解释,不成其为解释,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判断中国帝制晚期实际情况的基本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既不能给我们提供材料,也不能提供比较中国众王朝与其他前近代化社会,以及与20世纪中国政府所面对问题的分析框架。
诚然,个性确实在火耗归公的失败上起着作用,如同在它的实施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乾隆皇帝和他的先人相比,接受了更多的儒家教育熏陶,醉心于儒家的皇权神话。哈拉尔德·卡恩对儒家的皇权思想如何塑造乾隆皇帝行为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有两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是他过分渲染对其母亲的孝道,二是他近乎偏执地要做艺术和文学的支持者。被人视作仁义之君的愿望令他在处理雍正改革问题时犹豫不定。一方面,他担心支持火耗归公会被人视作有悖于古代圣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彻底否定他父亲煞费苦心实行的政策。最终,乾隆皇帝两全其美的努力确实破坏了火耗归公,但是它们不能对晚清再度出现的制度化的腐败负全部责任。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强加在合理化财政管理之上的帝制晚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桎梏,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华帝国的衰败,那么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对于帝国消除腐败的影响。火耗归公的一步步衰亡提供了一个帝制晚期改革局限性的极好例证,对此的分析将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用以评估保持足够收入任务的方法以及它常常运用的手段。如果政府确实试图消除腐败但以失败告终,那么对改革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帝制晚期政治的紧张状态是如何导致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国的衰败的。
显示全部信息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不久前,美国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都以鸦片战争第一声枪炮为开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1840年亦已成为评价国家过去历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由于仅仅关注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挑战之回应的失败,中国自身内在的演化进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领域,腐败的清帝国的幽灵铭刻在19世纪历史的编纂者心中,至今挥之不去。尽管我们不再说“不变的中国”(unchanging China),然而理解早期中国近代化经验的范式依然薄弱。腐败的帝国,由于陈旧的思想传统而与革新相暌违。结果,我们常常忽视这一历程的复杂性,并没有去探求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衰落的真正根源。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进行财政改革,以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臣民与统治者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调和作用但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他们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并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进行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世纪、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线模糊不清;在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他们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这使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加剧。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套财政制度,它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要求的财政制度。
清初财政改革事业的顶点是“耗羡归公”,这是在第三任皇帝即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实施的。各省官员被授权对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钱粮征收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即火耗),火耗存留在当地省份作为官员的“养廉”和“公费”。养廉银使得官员薪俸有了根本性的增加,同时可以使用公费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以及实施有益于当地的工程项目。
尽管火耗归公的概念简单,但它对中国财政管理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官僚体制内部,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足够的费用,消除了已经制度化的政府腐败。有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官员能够对地方开支进行预算并致力于地方建设工程的长期规划。此外,有了收入的保障,地方政府能够把许多服务及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而这些在帝国统治前数十年或被忽视或被委任于私人。
新财政制度所要解决的许多是前朝的遗存问题。明朝也曾多方努力消除腐败,但是除了“一条鞭法”的改革外,对重建国家财政机制没有什么建树。税收的货币化,这是“一条鞭法”的重要目标,是引发清初改革的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两个王朝在政府运行方面的差异大体可以解释清王朝为什么有能力在财政机构方面进行如此激烈的变革。
尽管明清两朝的官僚体制结构相同。但在明朝,意识形态的诉求(ideological appeals)在官员考核以及决策方面,起的作用要远为重要。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两个王朝皇帝的地位。明朝因其废除丞相而闻名,此举普遍被认为是帝制晚期对自治抬头的致命一击。尽管如此,大多数晚明统治者与操纵着中央官僚机构的那些文人们手中的傀儡相差无几。而另一方面,作为外族人,清初的统治者极少受传统君臣之礼的束缚,而且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帝王权威观念。与传统的儒学观念所强调的君主集权相比,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将皇帝置于权力更为集中的位置之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清初的皇帝们所起的直接作用是引进统治的新观念及新手段。到18世纪初,皇帝这一作用通过新制度的创立,比如奏折制度而得到强化,奏折制度既使皇帝得到信息,也增强了他对行政事务的控制。最后一点,与明朝相比,清王朝官僚机器本身更为集权,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的改革及保证皇帝对其实施的指导。
这些条件使18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解决中国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合理方法成为可能,但它们不能确保如此大胆的措施能够得以贯彻执行。处于被称为清朝盛世(High Ching)的每一位皇帝都是有才能及勤政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个性的差异以及各自统治期间政治气候的不同,对他们处理财政事务的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乾隆皇帝,盛世的最后一位君主,在统治过于宽仁的乃祖康熙皇帝和过于严猛的乃父雍正皇帝间极力寻求一种平衡。宽仁和严猛不单是这两位伟大帝王的不同风格。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满族人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统治。众所周知他拒绝打击腐败,但这可能是出于安抚占优势地位但还未顺从清朝统治的汉人官僚的需要。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则不再担心来自官僚或士人的责难。待他登极之时,中国统一,四海清平。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满族几近八十年的统治已经使他们在现实中除了清廷外别无忠诚对象,这些人的地位不但在于拥有地方上的财富和影响,也有赖于帝国赋予的官位与功名。雍正皇帝严刻、务实。但假如他统治的时期更早一些,那么他将不大可能采取实际上所采纳的合理化管理以及和腐败及士绅特权斗争的措施。
清朝盛世的和平与繁荣,部分要归功于火耗归公改革。不幸的是,尽管火耗归公对近代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终它还是失败了。19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斥腐败、被离心力量所破坏的国家,政府已日益衰落、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尽管如此,当真正了解在西方上升的世纪似乎冥顽不变的“传统”中国君主政体的时候,我们所探求的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会发生剧烈的改变:中国不总是如此。我们必须学会将帝制晚期的中国视为有生机的国家,为设计合理与高效的官僚体制自我的特有形式而奋斗。即便说火耗归公是一次失败的改革,那么我们也必须问个为什么。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视官僚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官僚阶层的道德堕落。现代批评家们也往往追随这一结论,面对政府严惩财政渎职官员的种种则例,学者们断言,清政府过于孱弱、懈怠而无法将之付诸实践,或是习惯势力过于强大,不论谁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都无法取胜。最终我们得出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中国是腐败的,所以中国是腐败的(China was corrupt because China was corrupt)。这样的解释,不成其为解释,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判断中国帝制晚期实际情况的基本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既不能给我们提供材料,也不能提供比较中国众王朝与其他前近代化社会,以及与20世纪中国政府所面对问题的分析框架。
诚然,个性确实在火耗归公的失败上起着作用,如同在它的实施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乾隆皇帝和他的先人相比,接受了更多的儒家教育熏陶,醉心于儒家的皇权神话。哈拉尔德·卡恩对儒家的皇权思想如何塑造乾隆皇帝行为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有两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是他过分渲染对其母亲的孝道,二是他近乎偏执地要做艺术和文学的支持者。被人视作仁义之君的愿望令他在处理雍正改革问题时犹豫不定。一方面,他担心支持火耗归公会被人视作有悖于古代圣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彻底否定他父亲煞费苦心实行的政策。最终,乾隆皇帝两全其美的努力确实破坏了火耗归公,但是它们不能对晚清再度出现的制度化的腐败负全部责任。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强加在合理化财政管理之上的帝制晚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桎梏,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华帝国的衰败,那么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对于帝国消除腐败的影响。火耗归公的一步步衰亡提供了一个帝制晚期改革局限性的极好例证,对此的分析将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用以评估保持足够收入任务的方法以及它常常运用的手段。如果政府确实试图消除腐败但以失败告终,那么对改革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帝制晚期政治的紧张状态是如何导致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国的衰败的。
显示全部信息
目录